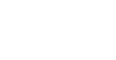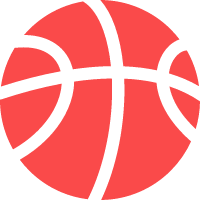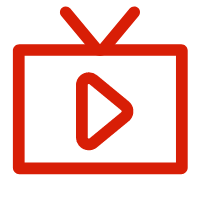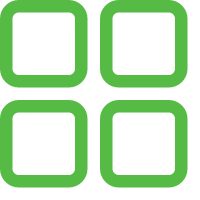勒费

勒费的跑道
跑道是红的,四百米一圈,像一条无限循环的带子。我跑在上面,脚步重复着单调的节奏,呼吸与风声混在一起。这重复里,藏着一种近乎残酷的真实——你无法欺骗跑道。你投入的每一分气力,它都记得;你松懈的每一瞬,它也都知道。终点线永远在那里,不近不远,衡量着一切。
这让我想起历史学家费尔南·布罗代尔提出的“长时段”概念。他将历史时间分为地理时间、社会时间与个体时间。在这跑道上,我正同时经历着这三种时间:脚下是千万年地质运动形成的恒定大地(地理时间);我所遵循的训练周期与竞赛传统,是体育文明数十百年积淀的节奏(社会时间);而我胸腔的灼烧、腿部的酸胀,以及每一次想要放弃却又抬起的步伐,则是我此刻全部的生命存在(个体时间)。跑道,成了时间的显形之物。
有时,在极度疲惫的恍惚中,我会感到一种奇异的抽离。那个拼命奔跑的“我”,仿佛暂时退场了。支配这具身体的,是更原始的东西:一种不服输的惯性,一种对秩序(比如必须跑完的计划)的服从,甚至是一种对“耗尽”本身的无言渴望。这不是哲学的沉思,这是身体在极限处的自我言说。勒费或许会认为,这种状态下,人得以短暂地逃离被定义的“自我”,触摸到某种更本质的生存状态——不是思考存在,而是以全部血肉之躯,去成为存在。
最后一圈,教练的哨音刺破黄昏。我奋力冲刺,像要挣脱所有时间的束缚。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,三种时间轰然合流。我瘫倒在草地上,世界只剩下心跳如鼓,以及天空无言的深蓝。跑道静默如初,它什么也没说,却已道尽一切。